在加拿大
7月7日,河南都市频道报道,四川达州9个少年被骗到缅甸做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在缅北,他们完不成业绩被“水管打、开水烫、电击······”据家长介绍,这几个孩子里最小的15岁,最大的刚成年不久,至今还在求救回国。
今年5月底,我进入一个200多成员的“家长群”,群里是来自全国各地、被骗去东南亚电诈公司的孩子家长,他们每天分享孩子被骗的经历,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互相鼓励。有不少家长的孩子还未成年,他们大多是初中辍学,部分在职业高中、技校读书,被相识的人以高薪工作为由骗走。
6月初,我在广西北海市见到一个15岁的少女,她今年2月底被骗去缅北,4月初被解救回国。我与她相处了几天,她像是这群偷渡少年的缩影,成长过程充满诱惑、危机,在辍学后、成年前这个夹缝年龄段里,像一粒尘埃漂浮于种种灰色角落。被骗去缅甸,只是其中一个结果。
记者|李晓洁
15岁女孩
第一眼见到周婷,不太容易看出她只有15岁。一头橙红色长发,是她半年前染的红发褪去后的颜色,现在头顶冒出几厘米黑。她化了妆,涂了口红,长长的眼线从眼尾伸出,显得眼睛更大。穿着时髦的白色泡泡袖连衣裙,长度到膝盖上方,右臂半露着一朵红花。在出租车后座,她说那是自己贴上去的纹身。我们在车内寒暄着高温,才6月初,广西北海市室外的空气浓热,没有风,路两旁的大王椰像站立的模型,一个个退到车窗后。
前一晚,周婷12点从KTV下班。这是她一周前刚找到的工作,在一家高级KTV会所做包厢公主,底薪5000,如果招揽到客户订包厢,再另算提成。她告诉老板自己17岁,身份证弄丢了,老板没多问,她便开始了“实习”。她觉得这份工作轻松,只需要在包厢里帮客人点歌、记账单,结束后打扫下房间卫生,无需陪酒。唯一的缺点是下班时间晚、不固定,有时等客人离开,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下班后,她通常用手机扫一辆共享电动车,在清凉的夜风里,骑十多分钟到小区。打开每月550元租金的单间房门,迎接她的是一只两个月大的拉布拉多犬。
“我姐妹花800块买的拉布拉多,懒得养就扔给我了,一开始我也不打算养的。”周婷声线有点低,显得更成熟。但说到养狗的趣事,她忽然提高音调:“每天晚上回来都遛它,结果早上起来我还是踩到狗屎,还当着我的面撒尿!”说到这,她一阵傻笑,让人想起她还是个孩子。看起来,她似乎在慢慢恢复自己的生活。

《狗十三》剧照
就在两个多月前,她还困在缅甸北部一个电信诈骗园区里。事情起源于今年2月底,刚过完年,周婷到广西北海市另一家KTV做包厢公主,一位曾经打工认识的男生联系上周婷,称自己在缅甸工作,月薪十万。“说那里还有兵哥哥带着枪保护他,很威风。”周婷相信了那个20岁左右的男生,因为对他印象不错。去年周婷在一家夜店型酒吧工作时,男生常接她上下班。
2月25日,周婷在对方的指导下,告诉家人自己要跟朋友去广东工厂打工。一周后,她在一个朋友群里说自己到缅甸了。群里一个女生不放心,联系上周婷的哥哥周毅。周毅在南宁一所本科学校读书,当晚11点,他联系上周婷时,妹妹还没意识到自己被骗:“先不回去,挣到钱再说”“工资一个月10万”。直到3月23日,想回家但却无法自由离开的周婷给哥哥发去所在园区位置,称需要赎金才能回国。最终,家人和公安确定了她具体位置后,凑齐12万赎金交给园区。4月3日,周婷登上了回国的班机。
跟周婷一样,经由国内边境线偷渡到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做电信网络诈骗的年轻人不是少数。其中,缅甸是电信网络诈骗组织数量最多的地方。根据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联席办”)统计,截止2022年3月,缅北(缅甸北部)电信网络诈骗窝点作案数量占境外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68.5%。从缅甸自首回国的诈骗人员中,偷越国境的占97%;在中缅国境线被拦截的偷越国境人员中,70%偷渡目的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
河南许昌市公安局的杜广雷对偷渡缅甸做电信诈骗的人员做过研究。他提到,因为中缅边境线上有上千条村庄和便道直通缅北,且缅甸国内有部分省、邦和特区由当地少数民族和地方武装管理,拥有自治权,而这些自治区与电信诈骗组织、偷渡犯罪组织存在利益关系,因此组织常受到当地庇护。杜广雷曾与100余名偷渡违法犯罪人员交流,对30多个犯罪团伙和典型案件中的1000名涉案人员(女性90人,男性910人)进行综合分析。他的研究数据显示,偷越国境违法犯罪人员中,农村居民占98%。他们受教育程度低。绝大多数为中、小学文化,本科文化只有1%。其中,20-30岁占56%,未成年占比7%。
但这份截止到2022年初的研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结束,很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孙霖在国内做协助被骗至东南亚同胞回国的解救工作,几个社交平台账号都叫“东南亚老司机回国咨询”。2020年至今,他和团队协助至少1000人从东南亚回国。他的感受是,疫情结束后这半年,偷渡到东南亚的未成年人比之前明显变多。如果范围再扩大点,00后成了主流。他今年解救一个15岁的男孩,是他这几年遇到年龄最低的偷渡人员。他分析,最近三年,国内重点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各个省、市、县下达非法滞留境外人员的劝返通告。但即便有警方的介入,回国也是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国内警方在缅北没有执法权,家长要先通过跟孩子联系,确认其所在园区位置后提供给警方,警方再找当地关系,安排交赎金,然后在缅北类似于公安局的机构登记、排队回国。“2020到2022上半年,回国人数特别多,最多的一天,我们安排了400人通过插队方式回国。回国的人多了,诈骗公司越缺人,就越疯狂地抢人,甚至买卖人口。缺乏社会经验的未成年人更容易被骗。”
5月底,我进入一个200多成员的“家长群”,群里是来自全国各地、被骗去东南亚电诈公司的孩子家长,他们每天分享孩子被骗的经历,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互相鼓励。这些家长的孩子们,大多是初中辍学,部分在职业高中、技校读书,被相识的人以高薪工作为由骗走。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乡村,或是留守儿童,与父母、亲属的关系淡薄,是周围人眼中的“问题少年”。6月初,我联系上周婷。她像是这群偷渡少年的缩影,成长过程充满诱惑、危机,被骗去缅甸,只是其中一个结果。

《模范出租车2》剧照
乡镇辍学生
周婷的家,在距离北海大约50公里的乡镇。坐上大巴车,18元,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这是附近几个乡镇里比较热闹的一个,全镇8万多人口,一条国道穿越镇中心,道路两旁拥挤着各种奶茶、小吃店,以及四五层高的居民自建楼。镇上有文化馆、图书室和剧团,还有几座十多层高的楼,一些KTV、娱乐场所开在那里。到了晚上,中心街旁一条一公里多长的小吃街开张,亮堂堂的,连隔壁镇的人也要来逛一逛。
虽然热闹,但周婷很少回镇上,她觉得无聊,“哪有市里大?”另一方面,她不想见到假期回家的继父。
周婷有“两个父亲”,她跟他们关系都不好。三岁时,母亲与生父离婚,原因是生父出轨、酗酒,喝醉后就砸烂身边的一切。当时周婷跟着母亲,8岁的哥哥跟着父亲去隔壁镇生活。之后,周婷没见过生父几次,她和哥哥周毅对生父的描述很一致:“只有恨”,他不支付周毅高中和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周毅靠贷款、助学金、不断兼职挣钱读书。逢年过节,周婷给生父发祝福,极少有回复。几个月前,从缅北解救周婷需要赎金,警察打电话给生父,希望他出3万,对方回复“我只有300你要不要?”回忆到这里,周婷骂了句脏话,说自己和哥哥几年前就删除了生父的联系方式。
大约小学一年级,周婷有了继父,他在广东打工,做体力活儿,一个沉默的男人,“什么话都憋着,跟谁也不说。”几年后,周婷有了妹妹,她能感觉到继父的变化,“对妹妹和他那边亲戚的孩子会笑,对我爱搭不理,喊他吃饭也不说话。”周婷已经两年多没跟继父说过一句话。

《如果蜗牛有爱情》剧照
如果只是一个不幸福的家庭,在镇上并不少见。周婷印象中,从小就听过不少附近乡镇的“杀妻案”,最近的一起发生在今年5月,镇上一个男人跟妻子吵架,怀疑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随后杀了妻子和孩子。在社交平台上输入周婷所在乡镇的名字,关联的词条就有过去几十年不同类型的凶案。在镇上,有一份稳定的、普普通通的生活似乎就令人满足。家长对孩子的期待也不高,读完义务教育,最好能考上普通高中,实在不行就去职校,至少安稳地度过成年前的阶段。周婷母亲就抱着这种期待,她希望学校能为孩子提供保护。
但周婷讨厌学校。她告诉我,自己小学时成绩中等,偶尔考试成绩下降,老师会用书本打她的脸,“很不尊重人”,她从那时起就不喜欢老师。小学毕业后,她有了手机,是母亲用旧了留给她的。她注册了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自己的照片。很快,一个看起来30多岁的陌生男人给她发私信,想跟她见面。她没有理会。但那个男人没有停止,直到她读初中,甚至辍学、换了账号后还在发信息骚扰她。升入初中,周婷成绩变差,交友范围也从校内蔓延到校外。她说不清自己怎么认识了一帮“精神小妹、精神小伙”,几乎每个人都染发,在瘦小的身体上纹身,抽烟喝酒、打架。同时,她更厌恶学校,觉得老师看她的眼神都是嘲讽。她也不喜欢同学间的氛围,“高一级学生欺负低一级,看谁不顺眼就打架,在背后说每个人的坏话,很幼稚。”初二上学期,一个同班女同学建议二人一起去广东打工。一个深夜,周婷收拾好行李箱从家里逃出,毫不留恋地离开了家、离开学校和乡镇。
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偷渡到缅甸的未成年,都跟周婷一样,是来自乡镇的辍学生,家长们习惯孩子忽然离开家,过段时间又突然回来。等意识到某次出走不对劲时,孩子往往已经身陷险境。

《通天塔》剧照
唐韵的儿子小烨今年15岁,偷渡去缅甸前,在成都县城的一所职高读高一。2月初跟同学到达缅甸,5月中旬被解救回国,赎金10万。唐韵告诉我,儿子小时候在农村由奶奶带大,他们一年见上两次。到县城读职高后,孩子离自己和老公打工的工地近了点,一家人周末才住到一起。小烨从小不爱读书,跟奶奶和家人的关系也比较淡漠。到了寒暑假,因为年龄太小,工厂、饭店等地方不收,他只能在家玩手机、跟乡镇其他男生乱逛。面对父母的指责,他会顶撞甚至离家出走。所以2月中旬,小烨一周多没回家,唐韵以为他跟朋友出去玩了。等三月联系上儿子,才知道他被网友骗,已经到了缅甸,计划“挣大钱”。
在社交网站上,小烨和朋友分享了刚到达缅甸后的几个视频。视频里,他们在靶场架起ak步枪射靶,在沙发包厢里共同吸一袋白色粉末,镜头一转,一个男孩手上拿着几沓百元人民币,配文是“等我花钱不看余额的时候,一定为你遮风挡雨”。异域、金钱、枪支、灯红酒绿似乎成为他们“独立”“有力量”的象征,虽然这个梦想会很快破灭。
从工厂到夜场
一天夜里12点多,周婷给我发信息,她当天要在KTV值班,一个包厢刚来了客人,估计要到凌晨两点多下班。她没吃晚饭,有点饿,问我能不能给她送吃的。半小时后,我到了她工作的KTV会所门口。
这是个“金碧辉煌”的地方,装修基调是金黄色和白色,大厅挑高三四米,墙壁和天花板上绘有希腊神话人物。正门入口处站着两个全身黑衣的年轻男保安,脖上挂着耳机,手里拿个对讲机,眼皮耷拉着,看起来有点疲倦。这家KTV附近一公里内,至少有6家同类型的娱乐会所,在夜间闪着高饱和度的荧光。在北海市,这样的娱乐场所很常见。老城区海边的广场,挨着开了三家大型夜店嗨吧,每家嗨吧门口竖着“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警示牌,一家嗨吧楼顶还高高竖起了五星红旗。而几十米外就是居民区和酒店,晚饭后常有居民遛狗、拎着音响在附近的广场唱歌。
我在KTV四楼的员工休息区见到周婷,她盘起头发,穿上白色半袖西装和黑色短裙,还有一双黑色细高跟鞋,看起来更成熟了。她甩开脚上的高跟鞋,换上拖鞋,不断说自己“饿死了”。原本这个休息区只有女生能进,但当晚老板外出,三四个看起来还是学生模样的男员工也进来,坐在沙发上打游戏。其中一个黑衬衣西裤的男生坐在周婷身边,他算是周婷的上司,瘦得皮包骨,两条胳膊上满是纹身,说自己22岁,“干夜场好几年了。”他和周婷聊天,开玩笑,趁周婷弯腰去捡地上的东西时,偷瞄她的胸部。吃完饭,周婷问男生要一支烟,点火前她瞄了我一眼,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抽烟,好像在试探我会不会阻止。

《漫长的季节》剧照
这就是周婷工作的场所。初二辍学这两年,她换过至少五六份工作,大多是在夜场,最久的一次工作了小半年,在广东一家嗨吧做营销,底薪3000,需要不断找客人进酒吧消费,按消费金额提成。
这并不是她最初想找的工作。周婷说,当初跟同学逃出家后,母亲报警联系到她,同意她不读书,但一定要回家,从事“安全的工作”。她的第一份工作,在附近乡镇看水果摊,一天一百多块,她嫌弃工作从早坐到晚,“无聊又累”,呆了两天,工资也不要就走了。后来她跟一位同样辍学的女同学去东莞找中介,中介给她一张假身份证,进了厂。在工厂给物品贴标签,吃住在员工宿舍,每月薪水4500,她和同学做了两个月,还是觉得太累,不自由,辞职了。
辞职后,周婷的同学认识个网友,说在酒吧工作轻松、工资高,俩人几乎没犹豫,进入了夜场。周婷说自己好奇心很重,很想看看在夜场工作到底是什么样。“都说不能去,我偏要去,家里人管不动我。我很倔,认定一件事就要做,除非我累了,不想做。”这之后,周婷回了几次家,又去广东进过一个月工厂。去年秋天,她到合浦县的嗨吧做气氛组(负责活跃酒吧气氛)。她曾想在县里一些“正规”奶茶店做服务员,但她丢了假身份证,很多地方不招收未成年人,只有夜场好像是唯一欢迎她的地方。在去缅甸前,她就在不同的夜场换工作,像一粒漂浮不定的尘埃。
周婷和朋友们都很想赶紧成年,赶紧离开这个辍学后、成年前的夹缝年龄段。他们想象成年人的生活不受限制,在社交平台上也有意无意模仿成年人。比如养宠物,有人在视频账号分享蓝猫,有人遛狗;他们喜欢被叫哥、姐,而不是妹妹弟弟;女孩们的衣服基本是短裙,黑色蕾丝和绸缎质;周婷有个“姐妹”跟男友合租,男友不让她工作,不让她跟其他男生接触,甚至不让她跟姐妹聚会,那个女生觉得这就是宠爱。

《通天塔》剧照
但周婷不这么认为,觉得“那样很傻”。她不喜欢同龄男生,“他们只知道打架,很幼稚”。在夜场工作,遇到毛手毛脚,让她陪酒、陪唱歌的男人,她直接拒绝。她曾遇到一个“姐姐”,让她跟“老男人”聊天、要点钱,她不愿意,“觉得恶心”,她也从未和男性去酒店过夜。身体是她在外讨生活的底线。在嗨吧做气氛组收入最高时,一天有2000块。这种时候,她给读书的哥哥、在镇上的母亲转几百。虽然法律意义上哥哥判给生父,但这个破碎的家里,她和哥哥、母亲三人互相依偎,每天都在微信上说几句话。
但夜场毕竟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地方,周毅和母亲常告诫周婷不要好奇心太重、被别人骗。去年,母亲刷抖音看到有未成年被骗到缅甸,还提醒女儿小心。但周婷当时完全没在意,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直到遥远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出国”
一开始,周婷对于偷渡一点也不怕。她瞒着家人,只背了个小包坐高铁到昆明。在昆明,一个蛇头(带路、组织偷渡出国的人)开辆小巴车接周婷,车上大约10个准备偷渡的人,只有周婷是未成年,其余看起来都是20出头的样子。蛇头嫌她年龄小,担心她到缅甸后待不久又要回家,她说自己一定要去,“我认定的事情就要做到底。”蛇头说去国外要做“杀猪盘”(利用网络交友进行诈骗),“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做就做啊。”就这样,她跟着一群成年人,坐车到西双版纳的中缅边境线,准备爬山偷渡。
现在回忆起爬山,周婷还觉得很“刺激”,跟她两年前逃离老家、决定不再读书一样刺激。他们绕过山脚下的警车,月光做指引,开始翻第一座山。山上有蛇头之前安排好的摩托车,周婷坐在后座。摩托车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穿行,她吓得尖叫,被村民看到报警。边境警察很快就追上来。周婷穿着裙子,弃车、下意识跟着逃跑,摔跤,起来再跑,左边大腿内侧至今还横斜着四道浅褐色伤疤。在翻过两三座山后,天亮了,他们也摆脱了警察,钻过一个破洞的边境铁丝网,到达缅甸。她第一次出了国。

图源 | 公众号“云南警方”
一位在云南某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告诉我,疫情三年是边境民警数量最多的时候。为了“动态清零”和打击偷渡,边境加大物理阻拦设施建设,通常是铁丝网和刺丝滚笼,每隔50米就有民警值守,极大打击了偷渡分子。但疫情结束后,被派驻边境的民警回到内地,值守人员不足,边境线总有不能及时修复的漏洞。
孙霖2019年偷渡到缅北,他记得当时还没有阻拦设施,“边境就像个菜园子,一个摩的,花20到50块就能送你到缅甸”。当时,孙霖在缅北开一家快餐食堂,主要给电诈园区提供盒饭,两餐饭80元。“缅北物价很高,一件国内几十块的T恤,都能卖4、500,我们从国内低价进菜,高价卖给园区,比在国内开饭馆挣钱。”也是那时,孙霖认识了几个缅甸本地人。
“缅北像国内三线城市,基本都说中文,大街上能听到老乡口音,绝大部分都是做电信诈骗。白天比较安全,到了晚上,我听到过几次枪声。不过现在不行了,前段时间听说有人在路上走,路边来个车就把人掳去园区。”孙霖语速很快,小拇指留着长指甲,几乎每隔一分钟就要回复手机上的信息。2020年,他成为非法滞留境外、被劝返的人员,他利用缅甸朋友的关系,协助跟他一样的滞留人员快速回国,还接应一些从园区逃出的同胞。2021年9月回国后,他自然而然做起了协助境外同胞回国的生意,目前团队核心人员有5人。他负责对接想回国的当事人,确认当事人园区位置后,只要对方逃出园区,他就能安排缅甸的朋友去接应,保证后续安全。疫情刚开始时,救一个人大概收费2000左右。
孙霖说,疫情前缅北园区管理并不严格,想逃出来不难。疫情期间,电诈公司缺人手,为了防止“员工”逃跑,园区开始装铁丝网,园内也有人24小时持枪巡逻。前年有一对在园区的四川夫妻想离开,联系孙霖在外面接应,但他们宿舍窗户全是钢筋。孙霖团队买了液压钳、拆开后放在夫妻点的外卖盒饭里送进园区,夫妻凌晨两点在宿舍组装钳子、拆钢筋,六点开了窗、逃出园区,坐上孙霖等人的摩托车逃走。因为之前诈骗业绩不好,“男的身上被打得都是黑紫色,女的胳膊上很多红色,被电棍电伤了。”

图@东南亚回国回国咨询
园区内的危险不止有体罚。25岁的陈晨是重庆垫江县人,今年2月被发小以开出租车的理由骗去老挝。被带到园区后,他意识到被骗,一直不配合工作,被关进“小黑屋”——一个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的小屋子。“他们把我手机没收,隔一两个小时就进来打我一次,不让我睡觉。偶尔给个盒饭,不给水喝,我只能喝水龙头的脏水。”陈晨告诉我,他被关了十多天后,身体出问题,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原本“公司”不会放他走,但碰巧前段时间有员工因糖尿病没被及时诊治去世,陈晨才被允许联系家人,在五月,交了8万赎金离开园区。
陈晨说,他被关进小黑屋前,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新人进入“公司”,“都是十几二十岁的样子,进了园区就出不去。”一个园区几十家“公司”,分散在几栋十多层高的楼里。园区内自成一体,食堂、宿舍、甚至小卖部都有。因为近两年国内严格打击电诈,陈晨所在公司主要做“欧美盘”,用翻译软件骗欧美人或华裔。如果业绩达到一定数额,公司会放烟花,还有可能带着员工外出逛逛。此外,上司还会让员工拉人头,骗一个国人偷渡成功,就有5500元收入。在公司,还流传一些“不能触碰的红线”。“不能暴露公司名字和位置、不能拍摄工作场景,如果被发现,很可能被打死,或者被关进水牢,半生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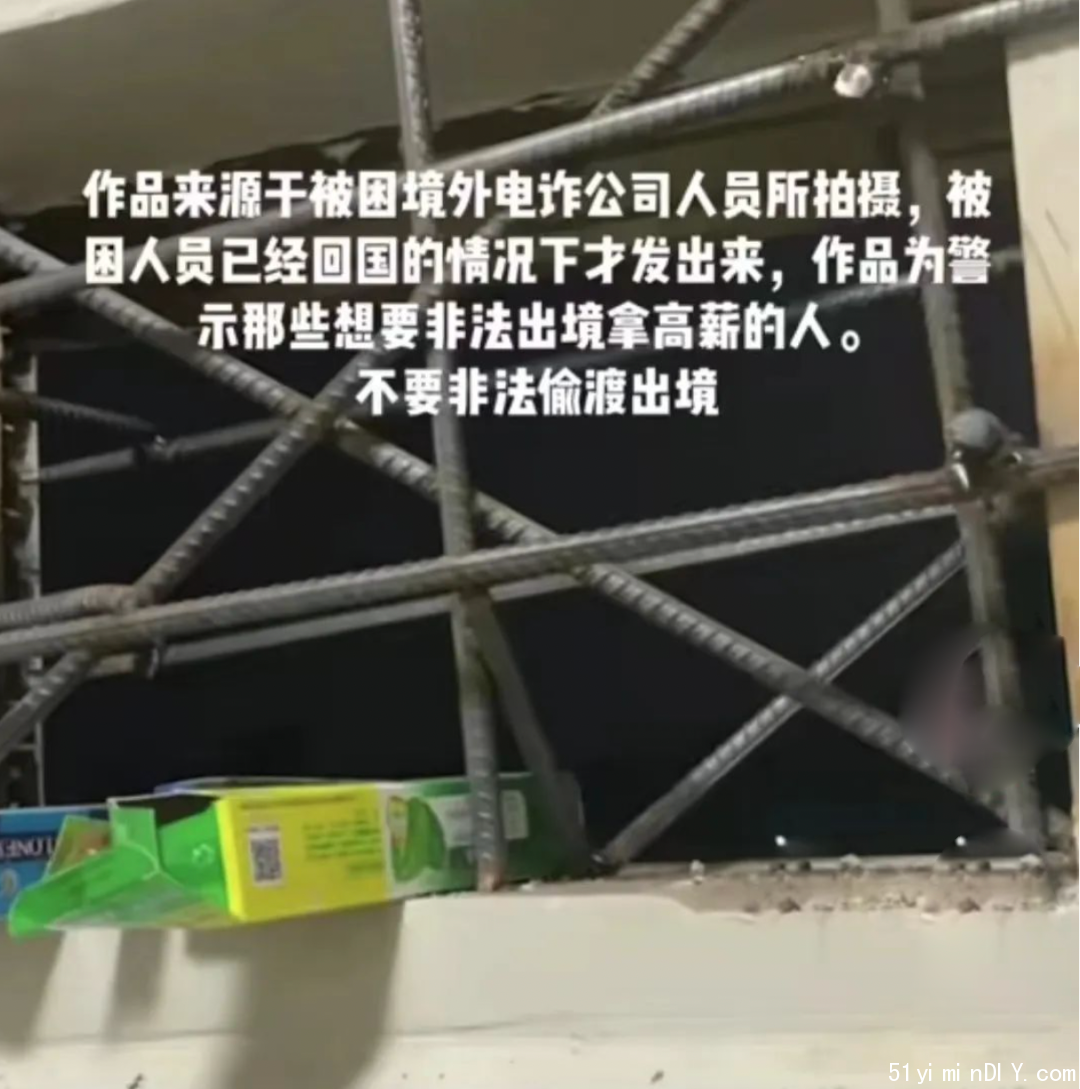
图@东南亚回国回国咨询
“最惨的是没有家人愿意出赎金。”孙霖说,他接触过一些家长,听说赎金数目后,再也没联系过他。他理解这群家长像惊弓之鸟,不少人都在求助的路上被骗过钱,不敢相信任何人。但因为逃跑难度变大,尽管团队的收费在业内不算高,也比三年前高了2-3倍。如果不逃跑,员工离开园区需支付的赎金也翻了倍。疫情前,赎金在3-5万左右,疫情后,赎金似乎没了准数。几个月前,孙霖听说一对父母为了救孩子,赔了4、50万才放人。也有家长拿不出高额赎金,放弃救孩子。
相比之下周婷算是幸运。她没被重度体罚,家人也借到了12万赎金。有一天,她所在小组因为诈骗业务不佳,一个上司拿水管粗的棍子打男生,女生罚深蹲。她看见一个男生被打得身上发紫,吓哭了,当晚就联系哥哥,想回家。4月3号,她走出园区,再一次跨过边境线,跟随合浦县警察,从西双版纳起飞,再转机到北海。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她坐在窗边,只觉得天空特别刺眼。
回国之后
6月初的一个周二下午,我在镇上一家奶茶店见到周婷的母亲。奶茶店有三四个沙发卡座,她和三个同龄人围着一个桌子喝饮料,吃腌鸡爪。紧挨着他们的卡座边,五六个未成年男生手机充着电,一边打游戏一边抽烟。烟味儿飘到这群母亲身边,她们瞥了一眼,没说什么,谁也不认识镇上这些不去上课的男生。
母亲穿着连衣裙,偏胖,有一双跟周婷很像的大眼睛,纹了粗眉。她说了好几次女儿“单纯,性格比较硬”,容易被骗,也很难被说服。“为了这个孩子,我没有一天安乐过,我希望她读书,打过骂过,也哄过,她逃走了,我不能把她拴在身上。”
“单纯”“没有社会经验”,这也是很多家长跟我们形容孩子的词汇。采访过程中,200多人的家长群里不断有新的家长进来,一遍遍在群里重复相似的问题:我能找谁求助?网上的志愿者能相信吗?你们花了多少钱?······有的家长甚至想独自出境,进入园区救孩子。最后,总有人出来呼吁家长团结起来自救,同时保持冷静。第二天,相似的讨论和呼吁又一次出现。

图@东南亚回国回国咨询
每一个被骗的孩子背后,都是一个愤怒、无助甚至绝望的家庭。很多家长学习搜索网络信息,第一次下载小红书,第一次使用Google、Telegram等软件。有家长被人以志愿者、民间救援的名义骗过钱。同时,他们还要承受网络带去的恶意。不止一位家长告诉我,他们发出的求助视频,总有人评论“孩子活该,已经死在境外”“不得好死”。一位家长说,孩子被骗后,“一家人浑浑噩噩,生活无色无味”。还有家长开始算命,想知道孩子是否活着。
最难承受的是来自家人的误解和指责。周婷母亲说,几个月前,刚得知女儿到缅甸时,她打电话给亲戚求助,每个人都怪她不会带孩子。她用尽几万块积蓄,卖掉了金项链和耳环,又借了几万块才凑够赎金。过程中第二任丈夫没有出力,他们的关系由淡漠转向一种隐隐的怨恨。她跟丈夫说好了离婚,小女儿给对方。她计划重新工作,当住家保姆,7月到北海一个客户家试用。“在北海做得不错,就去广州,那里工资高。干两年还完账,再干几年,攒够北海房子的首付给孩子,我再考虑自己。”谈话中,她有一种朴素的乐观,相信自己的双手可以重建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周婷也知道母亲将再次离婚,她支持母亲。在北海凌晨两点的海滩边,她牵着小拉布拉多,放下一些戒备。她说自己现在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朋友。刚从缅甸回北海时,原本想在初中读完剩下两个月,直到毕业。但老师调侃她的红头发和短裙,同学和昔日“姐妹”传言她被卖到缅甸当别人老婆,她呆了几天就离开学校。现在,她只相信母亲和哥哥,也觉得“对不起他们”。过几个月满16岁,她打算去考一个美容证书,之后也许可以开个美甲店。第一次,她有了攒钱的意识,计算自己的工资和花销,剩下的交给母亲,共同还债。说到这,海边有人放烟花,她跟着狗在沙滩上往烟花绽放的方向跑,边跑边发出憨憨的笑声。

图|作者 摄
如果生活就这样平静下去,未来也许会像周婷母亲计划得那样明确。但谁也不能对一个15岁女孩完全放心。深夜的海滩边,周婷收到一条信息,之前在缅北园区认识、还没回国的男生说无聊,邀请她打手机游戏。不久前,那个从六年级就骚扰她的男人又找到她的账号,发私信说给她8000块,只要二人过一夜。我离开北海的第二天,周毅告诉我,妹妹想去湖南打工,原因是北海最近查未成年人工作很严。当晚,周毅劝住了妹妹,但他消除不了心中的担忧:她现在不去了,但会不会跟之前去缅甸一样骗我?
(文中除杜广雷外,所有人物均为化名。实习记者罗云裳对本文亦有贡献)
·生活百科 捕获电力继电器与雪莉
·生活百科 逆变器电池的典型边距是什么?













